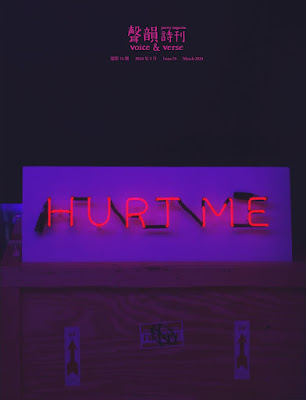影評人、書評人。著有《里爾克十論》、《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散文集《記憶散步》、詩集《記憶前書》、《記憶後書》及《記憶之中》,合著有《左文右武中師父 :劉家良功夫電影研究》,主編有《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新詩卷二》、《沉默的回聲》、《青春的一抹彩色——影迷公主陳寶珠:愛她想她寫她(評論集)》、《金庸:從香港到世界》、《五○年代香港詩選》、《香港短篇小說選2004—2005》、《2011香港電影回顧》、《讀書有時》三集、《民國思潮那些年》四集,合編有《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小說卷》、《香港文學與電影》、《香港當代詩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香港粵語頂硬上》及《香港粵語撐到底》等。2013及2025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獎(藝術評論、文學藝術)。2015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2024年參加香港國際詩歌之夜。2022至2025年擔任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長。現為香港文學評論學會主席、香港電台《開卷樂》主持、《聲韻詩刊》《方圓》編委。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12月30日
2024年12月27日
2024年12月12日
2024年12月1日
2024年11月15日
2024年11月11日
2024年11月6日
2024年11月5日
2024年11月1日
2024年10月29日
2024年10月26日
2024年10月17日
2024年10月2日
2024年10月1日
十月十講
1. 【香港國際詩歌之夜 |十五週年紀念 】「母語的邊界」討論會
時間:2024年10月3日(四)7:30 - 9:30 pm
地點:上海YOUNG劇場·綠盒子
4. 「故鄉與他鄉 ── 香港國際詩歌之夜 圓桌論壇:當下世界的創作者生態」
2024年9月27日
2024年9月20日
2024年9月11日
2024年9月1日
2024年7月15日
《里爾克十論》Ten Essays on Rilke
2024年7月14日
2024年7月12日
2024年7月3日
2024年6月22日
2024年6月21日
2024年6月14日
《全職乖孫》:生死之間
《全職乖孫》(How to Make Millions
before Grandma Dies)是悲喜劇,徘徊於人生必經的生老病死,以至關乎生活與生存的金錢問題。帕特波尼蒂帕特(Pat Boonnitipat)聚焦於泰國華人家庭三代人的關係。最老的婆婆代表了華人傳統,包括了宗教、誠敬、勤儉樸實的生活文化。但傳統世界並不盡善盡美,婆婆經歷了重男輕女、包辦婚姻的傳統陋習,她自己對於三個子女也有偏愛,慣壞了小兒子阿水,但她的生活也有秩序,每天晨早出門賣粥維生,努力工作,但一切隨著婆婆患了末期癌症,傳統世界也步入黃昏。
年輕一代當然屬於現代世界,明仔和他堂妹小梅都是聰明人,用他們的方法賺錢。小梅有護理能力,一力照顧爺爺,突破了重男輕女的限制,爺爺死後,根據遺囑獲得巨額遺產,從此生活無憂。明仔眼見堂妹成功爭取,就向婆婆埋手,照顧她,並希望獲得遺產。故事就是傳統世界和現代世界的對照、互動,以至個人從兩個世界中,思索倫理的關係。
倫理離不開情,而情感付出永遠無法對等,子女無可能報答母親無休止的,偉大的愛。婆婆愛大兒子阿強,但阿強是徹頭徹尾的現代人,他最關心的是一家三口核心家庭,他關心女兒教育,也覬覦遺產。婆婆為大兒子阿強犧牲甚大,但阿強似乎未能回報母親恩情,留下遺憾。婆婆也愛小兒子阿水,阿水不成器,或多或少也跟母親溺愛有關。婆婆對女兒似乎最不熱情,但女兒應該是對母親最有孝心的人,她也能夠理解寡婦的孤獨,對母親毫無一點金錢物質所求,電影中,傳統世界在母親和女兒之間無縫接軌。
《全職乖孫》獨特之處,是深刻刻劃婆孫關係,相對上相關題材的電影不是很多,可以參照的有《別告訴她》(The Farewell),可見拙文〈《別告訴她》──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華人社會的婆孫關係,當然千差萬別,祖母或外婆可以是傳統世界的權威人物,教導孫輩如何處世為人,就像《全職乖孫》開頭一家拜山時婆婆的形象。當然,婆婆也是慈愛者,婆孫之間畢竟隔了一代,婆婆對兒孫沒有太高的期盼以及太大的責任,而孫仔孫女小時候當然是天真爛漫,長大了就未必有機會和很長時間和祖輩交往。婆婆是慈愛的長者,因為她對孫仔的是愛完全不求回報,也不理會他將來會是怎樣的人。
《全職乖孫》在内容安排上首尾呼應,由拜山開始,又由拜山作結。婆婆送給明仔的白恤衫是重要意象,這代表了婆婆的期望和禮物,當初明仔隨手放開在一邊,但在片末就穿上了。石榴是另一重要意象,石榴中間多核,在華人社會寓意多子多孫,有果必有因,石榴就是華人家庭的象徵,角色的性格自有家庭倫理上的因果關係,苦口婆心,一切離不開金錢物質,但更離不開情感的牽連。
大概十年八載之間,看了好幾部GDH發行出品的泰國電影,包括了《出貓特攻隊》(Bad Genius)、《無痛斷捨離》(Happy Old Year)、《神速特攻隊》(Fast and Feel Love)、《第151 個朋友》(Not Friends),《全職乖孫》也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尤其具有生活質感的一部。
2024年6月2日
2024年6月1日
2024年5月28日
2024年5月24日
2024年5月20日
2024年5月18日
2024年5月13日
2024年5月1日
2024年4月14日
2024年4月5日
2024年4月2日
2024年3月19日
2024年3月8日
《特權樂園》── 夢想集中營
《特權樂園》(The Zone of Interest)是祖納芬基里沙(Jonathan Glazer)自編自導的作品,雖然說是改編已故英國作家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的同名小說,但內容幾乎不相干,一樣的是,小說和電影都以奧斯威辛集中營指揮官赫斯(Rudolf Höss)為主要角色。
《特權樂園》一開始是幾分鐘的黑畫面引子,只有音樂,我們進入一個歷史反思的空間,率先打開了聽覺而非視覺,事實上,電影的音響設計十分重要。電影沒有揭示血腥的殺人畫面,但暴力卻是每一刻都發生,觀眾聽到遙遠可聞的槍聲、人聲、狗吠聲,但看不到暴力與殺戮。遠方煙囪的煙,已經令人想到無數人喪失生命。暴力在無形之中。
電影的主角赫斯,表面上看是好丈夫、好爸爸,有五個子女,而赫斯之妻希穎(Hedwig)也將家園整理佈置得有秩序,環境得體和美觀,像樂園一樣。但他們的家對面,就是赫斯管理的奧斯威辛集中營。赫斯和希穎眼中只有工作與家庭生活,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反之,外婆逗留一晚就惴惴不安,而女僕在黑夜中外出,善意地留下一些水果食物。
我們看不到暴力,留下許多聯想空間,例如赫斯與女子的性關係,又例如希穎將囚犯的物品充公又交給家人,我們看不過程,還有,赫斯的兩個兒子在花園,兄長將弟弟關在溫室,令人想到猶太人被關進毒氣室。至於,赫斯晚上向女兒閱讀的格林兄弟童話《糖果屋》(Hansel and Gretel),也有殘酷暴力的一面。
《特權樂園》的結尾十分有力。赫斯調職到柏林附近的奧拉寧堡,繼續受命執行屠殺計劃,但他與家人暫時分開。赫斯獨自參加慶祝宴會,在電話中對妻子說用毒氣殺宴會廳中人的笑話,反映赫斯還有希穎,根本視人命如草芥。
離開辦公室時,赫斯突然間感到作嘔,在痛苦中,一時間他似乎想到一些事。突然間,電影跳接到現在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博物館,歷史見證著希特拉、赫斯,以及德國納粹惡名昭彰的大屠殺。單單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裡,就有超過一百萬人被殺害。在痛苦中,赫斯似乎重獲思考能力,個人良心發現,但其實他沒有,赫斯一路往下走,踏上他的地獄沉淪之路。
總括而言,《特權樂園》的主題,就是「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這在鄂蘭(Hannah Arendt)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惡之平庸性的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一書中,有深入的探究。
鄂蘭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結尾,才帶出惡的平庸性這個深刻的見解。所謂惡的平庸性,就是指艾希曼這種人,他們不是一心想作個惡人,他們完全不知自己在做什麼,他們並不愚蠢,只是喪失思考能力(thoughtlessness)。鄂蘭認為,「這種與現實隔閡、麻木不仁的情況,是引發災難和浩劫的元兇,遠比人類與生俱來的所有罪惡本性加總起來更可怕」。
赫斯的原型不只是歷史上的赫斯,還有受審的艾希曼。事實上,電影也提及了艾希曼的名字。這種人奉公守法,盡忠職守,而且服從命令,但對不公義、不人道的事,毫無思考和反應,體現了「惡的平庸性」,在極權統治下,這種人將國家元首和上司的指示貫徹執行,造成了可怕的浩劫。
《特權樂園》的赫斯和艾希曼一樣,在家庭、朋友之間,可能是一個好人,心理正常,並非變態。但在現實中就是屠殺者,在歷史中就是最終判處絞刑的重犯。
2024年3月1日
2024年2月19日
2024年1月28日
2024年1月26日
〈香港本土詩的傳統〉附言
首先要理解什麼是傳統,否則莫衷一是。
傳統不是有獎問答遊戲,不是鬥快講出答案,重點也不是某年某月某日,而是一個年代甚至更長時間,詩歌或文學風格面貌的建立。
舉例而言,如果說五十年代中葉開始,馬朗建立了香港現代主義傳統,他是以編輯(《文藝新潮》)、創作(發表在《文藝新潮》的詩和小說)、評論(〈發刊詞: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到我們的旗下來〉)、翻譯、獎項多項工作,有力地帶動同儕和後輩,共同建立傳統,影響力下及六十年代甚至以後。
在五十年代中葉之前,例如三十年代就有現代主義風格的作品和相關評論,時間早得多了,足足有二十年,但三十年代的詩人和作家未至於建構起香港現代主義傳統。當然,遭逢亂世,當時的客觀大環境實在不利作家和詩人生存。
傳,是指傳承,有帶動的意思,一方面帶動同道中人,另一方面也帶動後起之秀。馬朗帶動的同道中人有楊際光、李維陵等等,後起之秀有崑南、蔡炎培、王無邪和盧因等等。
《文藝新潮》發表了許多翻譯,包括艾略特(T. S. Eliot,又譯艾略脫)和威廉斯。馬朗翻譯了威廉‧卡洛士‧威廉斯〈紅輪手推車〉、〈快樂的牆紙上〉、〈貧窮〉三首詩,在《文藝新潮》第七期(1956年11月25日)刊出,又以介紹文字旁及威廉斯與艾略特之爭,馬朗在香港率先指出威廉斯新鮮明朗的新路線:
「他不停努力建造美國現代詩的新路線,極力提倡美國風格,不但反對承襲英詩傳統,甚至反對艾略脫等順從歐洲的潮流,而採用大量俚語,簡明幾致近乎原始的詞彙,絕對主張自由,被人目為『不文明』和『粗野』。事實上他的詩非常革命化,也非常新鮮明朗,雖然違反純詩的規則,以及太熱衷於側重美國地方色彩,但是他的格調顯著並有風骨,勝過技巧的賣弄,所以即使寫得太多,寫得太快,不夠精嚴,卻是每一首都幾乎成為現代文學的『迷歌』。」
後起之秀崑南(另有筆名葉冬)在《好望角》第五號(1963年5月)「William Carlos Williams紀念專輯」中,發表〈談威廉斯的詩風〉一文,繼續討論威廉斯。但對於香港本土詩更有影響的,不是威廉斯本人,而是威廉斯的風格和他帶動的美國詩壇後起之秀,就是也斯在《美國地下文學選》翻譯的Beat Generation詩人和Bob Dylan歌詞。
傳統的建立不是依賴一篇詩話文章,而是一班人群策群力,後來者傳承,繼往開來。
對一些人來說,傳統也不是好東西,所以大家不用爭。統是指正統,有排拒異議一面,強大的傳統也為後來者帶來壓力或焦慮,所以傳統建立之後,就有人反傳統。對於艾略特的影響和現代主義的技法,西西、古蒼梧在六十年代提出觀察甚至評論,都是先驅的聲音,難能可貴。道路修直了,還要有人行,以編輯、以創作、以評論、以翻譯,一起走下去。
關於七十年代的香港本土詩和生活化寫作,也斯、葉輝、羅貴祥、王良和、鍾國強、王家琪都寫過一些重頭文章,我不重複贅言。另外,拙文〈香港本土詩的傳統〉,是鍾國強詩評集《默讀餘溫》的導讀,最好不要與書過分切割,尤其密切的是〈本土詩的一種面向——以阿藍、關夢南、馬若詩為例〉一文。
見樹不見林,只著重一個人和時間年月日,可能不見大環境、大面貌,但如要看林,也難免看不到樹的細節,反正有人看樹,我就看林好了,順便也看看樹。樹林清靜,可以慢慢看、默默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