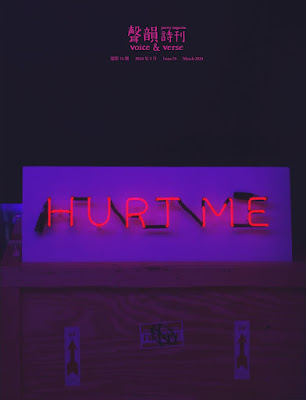影評人、書評人。著有《里爾克十論》、《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散文集《記憶散步》、詩集《記憶前書》、《記憶後書》及《記憶之中》,合著有《左文右武中師父 :劉家良功夫電影研究》,主編有《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新詩卷二》、《沉默的回聲》、《青春的一抹彩色——影迷公主陳寶珠:愛她想她寫她(評論集)》、《金庸:從香港到世界》、《五○年代香港詩選》、《香港短篇小說選2004—2005》、《2011香港電影回顧》、《讀書有時》三集、《民國思潮那些年》四集,合編有《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小說卷》、《香港文學與電影》、《香港當代詩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香港粵語頂硬上》及《香港粵語撐到底》等。2013及2025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獎(藝術評論、文學藝術)。2015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2024年參加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現為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香港電台《開卷樂》主持、《聲韻詩刊》《方圓》編委。
2024年3月19日
2024年3月8日
《特權樂園》── 夢想集中營
《特權樂園》(The Zone of Interest)是祖納芬基里沙(Jonathan Glazer)自編自導的作品,雖然說是改編已故英國作家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的同名小說,但內容幾乎不相干,一樣的是,小說和電影都以奧斯威辛集中營指揮官赫斯(Rudolf Höss)為主要角色。
《特權樂園》一開始是幾分鐘的黑畫面引子,只有音樂,我們進入一個歷史反思的空間,率先打開了聽覺而非視覺,事實上,電影的音響設計十分重要。電影沒有揭示血腥的殺人畫面,但暴力卻是每一刻都發生,觀眾聽到遙遠可聞的槍聲、人聲、狗吠聲,但看不到暴力與殺戮。遠方煙囪的煙,已經令人想到無數人喪失生命。暴力在無形之中。
電影的主角赫斯,表面上看是好丈夫、好爸爸,有五個子女,而赫斯之妻希穎(Hedwig)也將家園整理佈置得有秩序,環境得體和美觀,像樂園一樣。但他們的家對面,就是赫斯管理的奧斯威辛集中營。赫斯和希穎眼中只有工作與家庭生活,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反之,外婆逗留一晚就惴惴不安,而女僕在黑夜中外出,善意地留下一些水果食物。
我們看不到暴力,留下許多聯想空間,例如赫斯與女子的性關係,又例如希穎將囚犯的物品充公又交給家人,我們看不過程,還有,赫斯的兩個兒子在花園,兄長將弟弟關在溫室,令人想到猶太人被關進毒氣室。至於,赫斯晚上向女兒閱讀的格林兄弟童話《糖果屋》(Hansel and Gretel),也有殘酷暴力的一面。
《特權樂園》的結尾十分有力。赫斯調職到柏林附近的奧拉寧堡,繼續受命執行屠殺計劃,但他與家人暫時分開。赫斯獨自參加慶祝宴會,在電話中對妻子說用毒氣殺宴會廳中人的笑話,反映赫斯還有希穎,根本視人命如草芥。
離開辦公室時,赫斯突然間感到作嘔,在痛苦中,一時間他似乎想到一些事。突然間,電影跳接到現在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博物館,歷史見證著希特拉、赫斯,以及德國納粹惡名昭彰的大屠殺。單單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裡,就有超過一百萬人被殺害。在痛苦中,赫斯似乎重獲思考能力,個人良心發現,但其實他沒有,赫斯一路往下走,踏上他的地獄沉淪之路。
總括而言,《特權樂園》的主題,就是「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這在鄂蘭(Hannah Arendt)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惡之平庸性的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一書中,有深入的探究。
鄂蘭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結尾,才帶出惡的平庸性這個深刻的見解。所謂惡的平庸性,就是指艾希曼這種人,他們不是一心想作個惡人,他們完全不知自己在做什麼,他們並不愚蠢,只是喪失思考能力(thoughtlessness)。鄂蘭認為,「這種與現實隔閡、麻木不仁的情況,是引發災難和浩劫的元兇,遠比人類與生俱來的所有罪惡本性加總起來更可怕」。
赫斯的原型不只是歷史上的赫斯,還有受審的艾希曼。事實上,電影也提及了艾希曼的名字。這種人奉公守法,盡忠職守,而且服從命令,但對不公義、不人道的事,毫無思考和反應,體現了「惡的平庸性」,在極權統治下,這種人將國家元首和上司的指示貫徹執行,造成了可怕的浩劫。
《特權樂園》的赫斯和艾希曼一樣,在家庭、朋友之間,可能是一個好人,心理正常,並非變態。但在現實中就是屠殺者,在歷史中就是最終判處絞刑的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