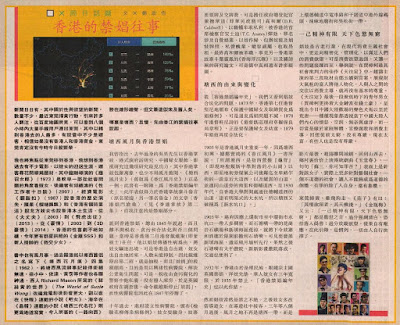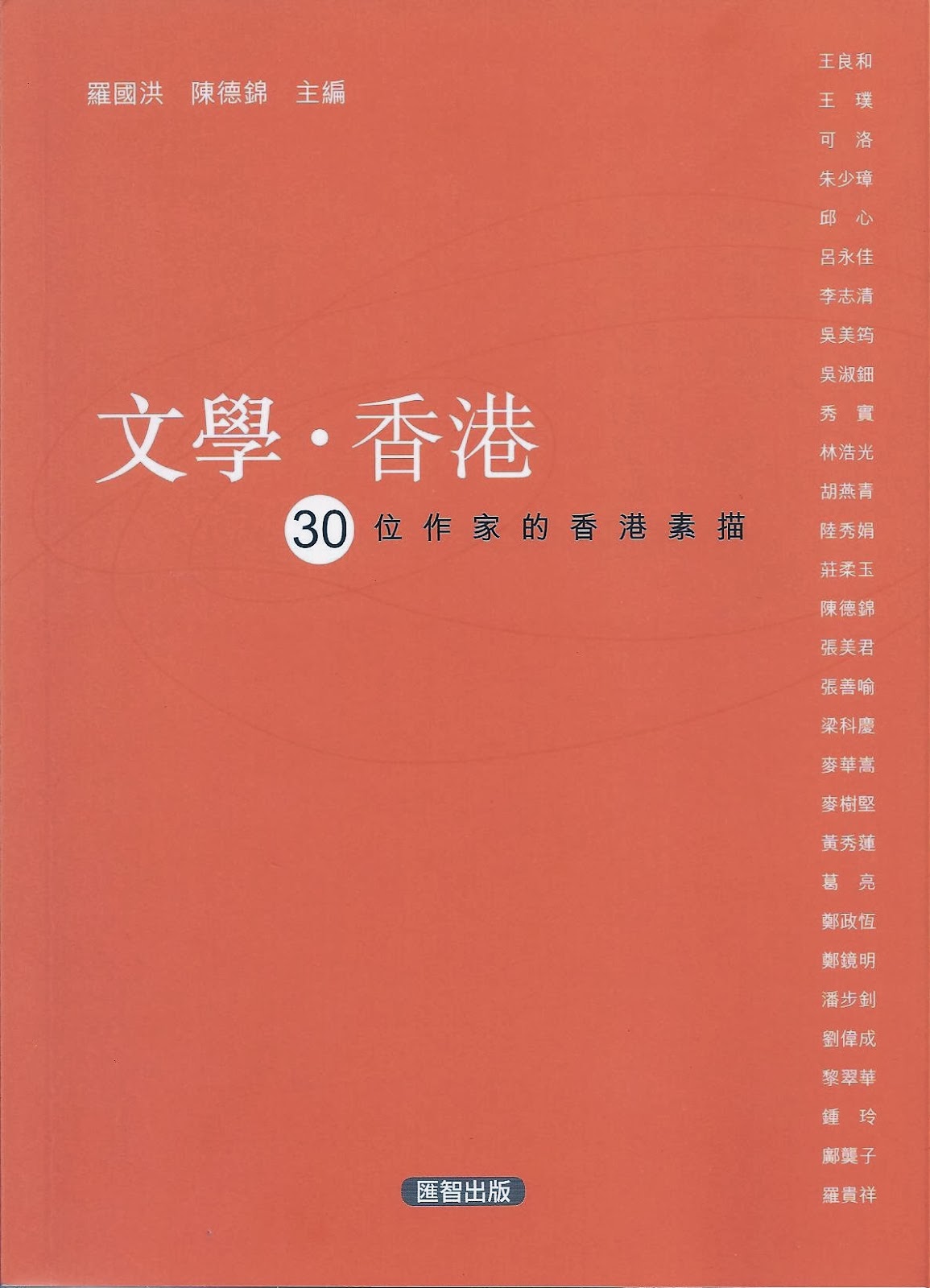影評人、書評人。著有《里爾克十論》、《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散文集《記憶散步》、詩集《記憶前書》、《記憶後書》及《記憶之中》,合著有《左文右武中師父 :劉家良功夫電影研究》,主編有《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新詩卷二》、《沉默的回聲》、《青春的一抹彩色——影迷公主陳寶珠:愛她想她寫她(評論集)》、《金庸:從香港到世界》、《五○年代香港詩選》、《香港短篇小說選2004—2005》、《2011香港電影回顧》、《讀書有時》三集、《民國思潮那些年》四集,合編有《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小說卷》、《香港文學與電影》、《香港當代詩選》、《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香港粵語頂硬上》及《香港粵語撐到底》等。2013及2025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獎(藝術評論、文學藝術)。2015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2024年參加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現為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香港電台《開卷樂》主持、《聲韻詩刊》《方圓》編委。
2014年2月18日
2014年2月7日
《LEGO英雄傳》:一切都很好
《LEGO英雄傳》彷彿有許多聲音,令人一下子不容易把握真正的信息。
從表面上看,《LEGO英雄傳》結合了電腦特技、定格動畫(stop motion)和3D技術,而且有打通了科幻片、美式英雄片、西部片、警匪片、歷險故事等類型元素,令人目不暇給。
電影有許多二元對立,按道理結構相當穩固,但創作人的詰問也不少,例如超級英雄與普通平民的對立,片中的主角是十分平凡的Emmet,他沒有甚麼特別創意,也沒有過人的才能,卻成為拯救行動的英雄人物,片中一方面建立英雄,集合眾多超級英雄(蝙蝠俠、超人、綠燈俠等等),但也反英雄,超級英雄都需要一介平民領導和救助。
另一個二元對立是好警和壞警(Bad Cop╱Good Cop),這個角色的設定似是來自《蝙蝠俠黑夜之神》的Two-Face,在兒童電影中警察總是好的(當然跟事實不符),但這一回卻是一個時好時壞,難分忠奸的警察,他好的一面給刪去了,但之後自己又建立良善的好人面孔(順筆一提,可愛貓也是有趣的角色,良善的貓學懂了憤怒)。
第三個二元對立是父與子,一說到父與子,令人想起家庭與傳承之外,又帶到權力的問題,而創作人明顯關心後者(其實因為屠格涅夫的小說《父與子》,父與子也是精神思想史的問題,伯林在《俄國思想家》一書中已有詳細剖析)。《LEGO英雄傳》最教我訝異的片段是,Emmet穿越了時空,由超真的LEGO世界,來到電影呈現的真實世界。原來邪惡的控制狂商人與父親是重象(怪獸家長?!),而許多事件是小孩子的想像。控制狂商人╱父親要用定型膠水將LEGO世界固定下來,最後卻是被小孩子感化,並回心轉意,那一刻我感覺到世界真的轉變了――以前只有父親教導兒子,現在倒過來是兒子教導父親了。
我們可以理解,在一個日漸平庸的世界裡,愈來愈重視社交網絡(多得互聯網帶來的便利),又愈來愈重視創意(電影強調creative,產業也重視creative,包括電影),後果就是人們不大重視傳統經驗,對權力之分也相當敏感,垂直的世界變成平等的世界。過去,偉大的靈魂建築師是老師,方法是教育。現在偉大的建築師,就靠將來的孩童了。在現實裡人們的這些想法,也透過動畫進入到LEGO的玩具世界了。甚至,電影中的主題歌Everything Is Awesome是例牌的正面信息,強調團結與夢想,而蝙蝠俠的歌Untitled Self Portrait卻有「黑暗,冇父母」的歌詞,兩種聲音在credit中先後出現。
片中的最強武器膠水與最強的對抗物膠蓋,是最後的二元對立,似是強調制衡與協作,父子之間的關係就這樣固定了。
《LEGO英雄傳》有許多聲音,信息上討好了孩子和年輕人,視覺效果就討好了成年人,而最開心的就是kidult,還有自由的現代人。
從表面上看,《LEGO英雄傳》結合了電腦特技、定格動畫(stop motion)和3D技術,而且有打通了科幻片、美式英雄片、西部片、警匪片、歷險故事等類型元素,令人目不暇給。
電影有許多二元對立,按道理結構相當穩固,但創作人的詰問也不少,例如超級英雄與普通平民的對立,片中的主角是十分平凡的Emmet,他沒有甚麼特別創意,也沒有過人的才能,卻成為拯救行動的英雄人物,片中一方面建立英雄,集合眾多超級英雄(蝙蝠俠、超人、綠燈俠等等),但也反英雄,超級英雄都需要一介平民領導和救助。
另一個二元對立是好警和壞警(Bad Cop╱Good Cop),這個角色的設定似是來自《蝙蝠俠黑夜之神》的Two-Face,在兒童電影中警察總是好的(當然跟事實不符),但這一回卻是一個時好時壞,難分忠奸的警察,他好的一面給刪去了,但之後自己又建立良善的好人面孔(順筆一提,可愛貓也是有趣的角色,良善的貓學懂了憤怒)。
第三個二元對立是父與子,一說到父與子,令人想起家庭與傳承之外,又帶到權力的問題,而創作人明顯關心後者(其實因為屠格涅夫的小說《父與子》,父與子也是精神思想史的問題,伯林在《俄國思想家》一書中已有詳細剖析)。《LEGO英雄傳》最教我訝異的片段是,Emmet穿越了時空,由超真的LEGO世界,來到電影呈現的真實世界。原來邪惡的控制狂商人與父親是重象(怪獸家長?!),而許多事件是小孩子的想像。控制狂商人╱父親要用定型膠水將LEGO世界固定下來,最後卻是被小孩子感化,並回心轉意,那一刻我感覺到世界真的轉變了――以前只有父親教導兒子,現在倒過來是兒子教導父親了。
我們可以理解,在一個日漸平庸的世界裡,愈來愈重視社交網絡(多得互聯網帶來的便利),又愈來愈重視創意(電影強調creative,產業也重視creative,包括電影),後果就是人們不大重視傳統經驗,對權力之分也相當敏感,垂直的世界變成平等的世界。過去,偉大的靈魂建築師是老師,方法是教育。現在偉大的建築師,就靠將來的孩童了。在現實裡人們的這些想法,也透過動畫進入到LEGO的玩具世界了。甚至,電影中的主題歌Everything Is Awesome是例牌的正面信息,強調團結與夢想,而蝙蝠俠的歌Untitled Self Portrait卻有「黑暗,冇父母」的歌詞,兩種聲音在credit中先後出現。
片中的最強武器膠水與最強的對抗物膠蓋,是最後的二元對立,似是強調制衡與協作,父子之間的關係就這樣固定了。
《LEGO英雄傳》有許多聲音,信息上討好了孩子和年輕人,視覺效果就討好了成年人,而最開心的就是kidult,還有自由的現代人。
2014年2月6日
2014年2月5日
2014年1月23日
2014年1月21日
布拉姆斯匈牙利之夜:第五屆香港國際室內樂音樂節一瞥
不論是電影界、音樂界或是戲劇界,將多個項目統合成電影節、音樂節或是戲劇節,是大勢所趨,在宣傳人員看來,當然是方便奏效;在宣傳人員看來,當然是折扣更多;在策劃人員看來,當然是展現功力了――若然節目不是直接進口的舶來品。
聚焦古典音樂界。過去一年,我想起幾個音樂節――聲蜚合唱節是合唱管弦樂音樂節,有大師班和音樂會(例如跟香港小交響樂團合作的海頓《創世紀》,相當成功);香港管弦樂團的馬捷爾系列和舒曼系列,都近似音樂節的模式,以指揮或作曲家為單位,輕易地將節目組合。然而,以節目編排而論,香港國際室內樂音樂節就最為成功。
香港國際室內樂音樂節來到第五屆,自2012年第三屆開始,由著名小提琴家林昭亮首次擔任音樂節的藝術總監(開首由大提琴家李垂誼掌舵),第三屆的焦點是譚盾的《鬼戲》,第四屆有寧峰、陳薩及海倫‧葛莉茉(Hélène Grimaud)、第五屆的重點大概是俄國小提琴好手列賓(Vadim Repin),印象中三年前他跟港樂合作演奏布拉姆斯小提琴協奏曲,而他的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協奏曲在芸芸經典錄音中,已站穩一席之地。
室內音樂節主要有七場音樂會,曲目編排甚見心思,如果你已看厭了例牌的本地音樂會節目,這幾場音樂會的曲目足夠令人眼前一亮,尤其是列賓與友共樂(林昭亮和列賓合奏Prokofiev的Sonata for two violins in C、Shostakovich的Piano Trio no.2,以及Taneyev的Piano Quintet in G minor!),還有閉幕音樂會(Vivaldi的Concerto for Four Violins in B
minor!)等等,都夠吸引,以下只集中布拉姆斯匈牙利之夜談談。
當晚由赫德里希(Augustin Hadelich)和霍夫曼(Gary Hoffman)的高大宜(Kodaly)小提琴與大提琴二重奏(Duo for violin and cello, op.7)開首,然後是兩首布拉姆斯,分別是諏訪內晶子、王健、梁喜媛合作第二鋼琴三重奏(Piano trio no.2 in C,
op.87),哈華(Burt Hara)和米羅弦樂四重奏(Miro Quartet)演奏B小調單簧管五重奏(Clarinet
Quintet in B minor, op.115)。
高大宜的作品恰恰在一百年前面世,為音樂會帶來二十世紀音樂的角度,也以地道的匈牙利音樂打頭陣,再轉入深受匈牙利音樂影響的布拉姆斯室內樂,順理成章,也別具巧思。
高大宜的二重奏只有兩件弦樂器,重點大概在於樂器的對話,旋律線條的發展和表現力,也可見匈牙利的民族樂風,赫德里希和霍夫曼都相當用心,熱情而緊湊的演繹相當壓場,而且保留了來自民間的粗獷感興。
布拉姆斯的第二鋼琴三重奏是全晚的亮點,教人感動。此曲作於1880至1882年之間,這兩三年間布拉姆斯創作了兩首序曲和第二鋼琴協奏曲,這首鋼琴三重奏也同樣上乘。我一直聽Katchen╱Suk╱Starker的經典版本,相較而言,諏訪、王健、梁喜媛也帶給我驚喜,尤其是王健的演出幾乎可以跟Janos Starker匹敵,諏訪和梁喜媛也相當出色,三人做到細緻中蘊藏表現力,不時有火花,尤其是第二樂章的主題與變奏,小提琴與大提琴以八度音平行前進,奏出主題旋律,非常合拍,悲劇感觸教人難忘,到C段的第三次變奏,布拉姆斯按主題再發展,小提琴與大提琴的十六分音符跳音演繹,音樂轉住戲劇性,兩位樂手也充滿強勁表現力。之後的第三樂章諧謔曲和第四章終曲,急快速度之下也十分流暢。總而言之,雖然有經典版本在手,諏訪、王健、梁喜媛的演繹,證明了現場的感染力不可替代。
音樂會的下半場是B小調單簧管五重奏,是布拉姆斯晚年的作品。哈華和米羅弦樂四重奏的表現還可,但跟上半場的演出相比卻是失色,他們的演繹保守平淡,樣樣恰如其分卻略欠火花,第二樂章開始時甚至有點混亂,幸好此樂章中單簧管的演出夠好,拾回狀態。
最後一提香港國際室內樂音樂節的一眾好手,不少曾跟小交和港樂合作,難得聽到他們演奏室內樂,而不是再聽例牌貨的大路協奏曲。我十分期望第六屆香港國際室內樂音樂節,繼續支持,繼續精彩。
2014年1月15日
《救火英雄》:沖天大火災
2014,又是新一年,一月開頭,最出色的是兩部法語藝術片:《接近無限溫暖的藍》(Blue is the Warmest Colour)和波蘭斯基的新作《玩謝大導演》(Venus in Fur),然而我決定以香港本土電影《救火英雄》,開展今年的影評書寫。
《救火英雄》是郭子健的新作,他原來以《野•良犬》和《青苔》嶄露頭角,跟鄭思傑合導的《打擂台》更獲得一片掌聲,可是隨後的《為你鍾情》以及跟周星馳合導的《西遊•降魔篇》未見突破,《救火英雄》也只是稍為回復狀態。
顧名思義,本片是關於消防員的災難片,去年彭氏兄弟的《逃出生天》教人不敢恭維,《救火英雄》則無疑勝過一籌了。然而,火災片不易拍得好,因為技術要求較高,也容易跌入公式化和煽情的窠臼,自從四十年前的名作《沖天大火災》(The Towering Inferno)以來,火災片未見重大進境,近來韓國片《火海108》也只算是中規中矩。
眼前的《救火英雄》確有濫調陳腔之處,例如余文樂不顧一切進入火場拯救兒子、譚耀文這類自私自利的角色設計、全城大停電危機等等。然而電影也擁有一些優點,例如以煙為中心意象、細心刻劃中層員工的壓力、強調男性之間的情義、前線人員專業、犧牲精神等等,這些優點都暗暗地鼓勵了香港人團結互助的精神,也讚許專業人員堅守崗位。
《救火英雄》帶出危機下的人性,包括人的迷失、自私、勇敢和毅力,創作人嘗試描繪深刻一點的範疇,可是有時講得太白,而且枝葉蔓衍,情勢太大,未算集中,又似乎是剪接方面未做到很到位,欠缺平衡和節奏。當然,結尾謝霆鋒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抽煙至彈煙一段頗有神采,可是這個水平的段落不多,總的來說《救火英雄》並不如幾年前的《打擂台》般教大家振奮。
回頭看2013年香港本土電影(總體數量應該跌破五十部的關口了),最好的電影都是強調香港人打不死的精神,例如《狂舞派》、《激戰》和《掃毒》,巧的是這些電影的票房成績都很好,得到觀眾擁戴,把握到大眾的心理認同。此外一些電影突出本土氣息,卻比較刻意或者低俗,其實並無甚麼正面意義。另外,又有一些電影強調了重大災難與危機,最近幾個月的《末日派對》、《救火英雄》和《風暴》都是例子,明眼人都可以看見香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面臨很大衝擊,但願新的一年本土民氣凝聚,團結一致,抵禦內部和外來的危機吧。
《救火英雄》是郭子健的新作,他原來以《野•良犬》和《青苔》嶄露頭角,跟鄭思傑合導的《打擂台》更獲得一片掌聲,可是隨後的《為你鍾情》以及跟周星馳合導的《西遊•降魔篇》未見突破,《救火英雄》也只是稍為回復狀態。
顧名思義,本片是關於消防員的災難片,去年彭氏兄弟的《逃出生天》教人不敢恭維,《救火英雄》則無疑勝過一籌了。然而,火災片不易拍得好,因為技術要求較高,也容易跌入公式化和煽情的窠臼,自從四十年前的名作《沖天大火災》(The Towering Inferno)以來,火災片未見重大進境,近來韓國片《火海108》也只算是中規中矩。
眼前的《救火英雄》確有濫調陳腔之處,例如余文樂不顧一切進入火場拯救兒子、譚耀文這類自私自利的角色設計、全城大停電危機等等。然而電影也擁有一些優點,例如以煙為中心意象、細心刻劃中層員工的壓力、強調男性之間的情義、前線人員專業、犧牲精神等等,這些優點都暗暗地鼓勵了香港人團結互助的精神,也讚許專業人員堅守崗位。
《救火英雄》帶出危機下的人性,包括人的迷失、自私、勇敢和毅力,創作人嘗試描繪深刻一點的範疇,可是有時講得太白,而且枝葉蔓衍,情勢太大,未算集中,又似乎是剪接方面未做到很到位,欠缺平衡和節奏。當然,結尾謝霆鋒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抽煙至彈煙一段頗有神采,可是這個水平的段落不多,總的來說《救火英雄》並不如幾年前的《打擂台》般教大家振奮。
回頭看2013年香港本土電影(總體數量應該跌破五十部的關口了),最好的電影都是強調香港人打不死的精神,例如《狂舞派》、《激戰》和《掃毒》,巧的是這些電影的票房成績都很好,得到觀眾擁戴,把握到大眾的心理認同。此外一些電影突出本土氣息,卻比較刻意或者低俗,其實並無甚麼正面意義。另外,又有一些電影強調了重大災難與危機,最近幾個月的《末日派對》、《救火英雄》和《風暴》都是例子,明眼人都可以看見香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面臨很大衝擊,但願新的一年本土民氣凝聚,團結一致,抵禦內部和外來的危機吧。
2014年1月10日
2014年1月9日
2014年1月2日
2013我的十大電影
《愛是神奇》(To the Wonder,Terrence Malick)
《風起了》(宮崎駿)
《末世列車》(奉俊昊)
《誰調換了我的父親》(是枝裕和)
《引力邊緣》(Gravity,Alfonso Cuarón)
《我不是拉登》(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Mira Nair)
《東京家族》(山田洋次)
《誣網》(The Hunt,Thomas Vinterberg)
《那年遇上世之介》(沖田修一)
《凱撒必死》(Caesar Must Die,Paolo and Vittorio Taviani)。
《風起了》(宮崎駿)
《末世列車》(奉俊昊)
《誰調換了我的父親》(是枝裕和)
《引力邊緣》(Gravity,Alfonso Cuarón)
《我不是拉登》(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Mira Nair)
《東京家族》(山田洋次)
《誣網》(The Hunt,Thomas Vinterberg)
《那年遇上世之介》(沖田修一)
《凱撒必死》(Caesar Must Die,Paolo and Vittorio Taviani)。
2013年12月11日
《阿信的故事》:命運是對手永不低頭
今年的日本電影特別好看,屈指一算,《東京家族》、《那年遇上世之介》、《神探伽俐略2:真夏方程式》、《北方的金絲雀》、《10億懸賞追殺令》、《誰調換了我的父親》、《圖書館戰爭》、《風起了》等都屬佳作,而《阿信的故事》也不例外,電影是為了紀念電視劇版本三十週年而攝製,也秉承了原初成長故事的奮鬥精神。
《阿信的故事》充滿著對老價值和舊時代倫理關係的懷戀,滲透著一些儒家傳統文化的氣息,人的一生,就是老老實實、勤勤懇懇的過活,不為個人權利,只為工作和家人獻身,任勞任怨,持守高尚的道德標準――阿信的人生不是一個故事,而是可以上升為民族魂的精神敘事,散發著東方倫理的核心價值。電影中,阿信名之為信,訓為誠信、信念、信仰,正是一錘定音,也由於阿信的個人信念,具體落實有血有肉的生活之中(而不是口號化的樣板),難怪阿信的故事可以感動到東亞文化圈的老百姓。
阿信生於日本山形縣的貧窮家庭,少小離家就當女傭,管家對阿信相當苛刻,更誣蔑阿信偷錢,阿信離開東家,在風雪中的荒山暈倒,為逃兵俊作所救,在山上,俊作教阿信讀書識字,也透過與謝野晶子致弟弟的名詩〈你不要死去〉,將反戰的思想灌輸給阿信。後來俊作被憲兵殺害,阿信回家後再次離家,到加賀屋當女傭,為主人八代邦所賞識,也跟加賀屋的加代小姐化解誤會,成為朋友,而最後阿信回家奔喪,並再一次離家工作去。
《阿信的故事》是成長故事,小女孩要離家、工作、遇到挑戰和挫折,再次回家、離家、工作,循環反復的歷練以至個人成長(不單季節在循環,其實祖母給阿信的圓幣也是循環的象徵,當然又可看作人為生活生存而奮鬥的象徵),而導演的拍攝手法則傾向沉穩、謹慎、誠敬,內在精神和外在表現做到表裡如一,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阿信是二十世紀的活歷史,電影版只拍了阿信的童年,阿信不爭取個人利益,對受苦有一種不言而喻的執迷,影片並不歌頌民族主義,一心回到傳統,也肯定母愛與女性的奉獻。
回頭看我們的香港,獅子山下精神,曾經是主流論述,成就了香港奇蹟。主流論述凝聚了共識,點出社會的發展方向,大家不問出身,同舟共濟,拼搏奮鬥,永不低頭,終將取得成功。可是,在回歸後,我們感覺到獅子山下精神一步步成為濫調,主流共識解體,社會原子化,核心價值受到衝擊,發展主義受到質疑,種種霸權、特權和教育商品化令社會流動性凝滯,中產面對下流化壓力,又也許最近的電視牌照事件,象徵了獅子山下精神的徹底破滅。
《阿信的故事》充滿著對老價值和舊時代倫理關係的懷戀,滲透著一些儒家傳統文化的氣息,人的一生,就是老老實實、勤勤懇懇的過活,不為個人權利,只為工作和家人獻身,任勞任怨,持守高尚的道德標準――阿信的人生不是一個故事,而是可以上升為民族魂的精神敘事,散發著東方倫理的核心價值。電影中,阿信名之為信,訓為誠信、信念、信仰,正是一錘定音,也由於阿信的個人信念,具體落實有血有肉的生活之中(而不是口號化的樣板),難怪阿信的故事可以感動到東亞文化圈的老百姓。
阿信生於日本山形縣的貧窮家庭,少小離家就當女傭,管家對阿信相當苛刻,更誣蔑阿信偷錢,阿信離開東家,在風雪中的荒山暈倒,為逃兵俊作所救,在山上,俊作教阿信讀書識字,也透過與謝野晶子致弟弟的名詩〈你不要死去〉,將反戰的思想灌輸給阿信。後來俊作被憲兵殺害,阿信回家後再次離家,到加賀屋當女傭,為主人八代邦所賞識,也跟加賀屋的加代小姐化解誤會,成為朋友,而最後阿信回家奔喪,並再一次離家工作去。
《阿信的故事》是成長故事,小女孩要離家、工作、遇到挑戰和挫折,再次回家、離家、工作,循環反復的歷練以至個人成長(不單季節在循環,其實祖母給阿信的圓幣也是循環的象徵,當然又可看作人為生活生存而奮鬥的象徵),而導演的拍攝手法則傾向沉穩、謹慎、誠敬,內在精神和外在表現做到表裡如一,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阿信是二十世紀的活歷史,電影版只拍了阿信的童年,阿信不爭取個人利益,對受苦有一種不言而喻的執迷,影片並不歌頌民族主義,一心回到傳統,也肯定母愛與女性的奉獻。
回頭看我們的香港,獅子山下精神,曾經是主流論述,成就了香港奇蹟。主流論述凝聚了共識,點出社會的發展方向,大家不問出身,同舟共濟,拼搏奮鬥,永不低頭,終將取得成功。可是,在回歸後,我們感覺到獅子山下精神一步步成為濫調,主流共識解體,社會原子化,核心價值受到衝擊,發展主義受到質疑,種種霸權、特權和教育商品化令社會流動性凝滯,中產面對下流化壓力,又也許最近的電視牌照事件,象徵了獅子山下精神的徹底破滅。
訂閱:
文章 (Atom)